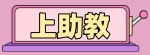
和球搭子最后一次打球
《最后一个球》
球馆的灯依旧亮得刺眼,塑胶地板上还留着几道新鲜的擦痕。我和老张像往常一样站在球台两侧,谁都没提这是最后一次。
他的发球还是那么刁钻,我勉强接住,球在网带上轻轻一蹭,落在他那边。老张笑了:“运气不错啊。”我也笑,可喉咙发紧。
我们打了十年球,从大学体育馆的破球台打到这家收费不菲的俱乐部。他总说我的反手像抡锄头,我说他的正手弧圈像老太太甩腰鼓。后来他查出腰椎间盘突出,医生建议他别打了,他硬是撑到女儿考上大学。
最后一局打到10平,他忽然停下,从兜里掏出个小铁盒:“当年赢你的‘红双喜’三星球,还剩最后一个。”塑料球早就取代了赛璐珞,这颗旧球在灯光下泛着陈年的哑光。
21:23,球擦边落地。老张弯腰捡球的动作很慢,像电影里的慢镜头。他把球捏在手里看了看,突然扔给我:“留着吧,下次…”话没说完,自己先摆了摆手。
球馆外在下雨,我们都没带伞。
与和球搭子最后一次打球相关的问题
其他问题
- 武汉寻找COS搭子,开启你的二次元冒险之旅
- 什么是“酒搭子榴园”?
- 在布里斯班想找散步搭子,有什么推荐的方式或平台吗?
- 在普吉岛找旅行搭子,一般通过哪些渠道比较靠谱?
- 在《和平精英》中,搭子滴滴有什么作用?**
- 探寻琅勃拉邦搭子的独特魅力
- 在木渎附近想找健身搭子,有没有推荐的健身房或者一起锻炼的小伙伴?
- 《王者搭子Q区V10:当游戏社交遇上“钞能力”》
- ### 王者游戏搭子照片:记录游戏中的友情与回忆
- 重庆有哪些好玩的密室逃脱推荐?
- 探索“Lo娘旅游搭子”的奇妙之旅
- 甜酷风穿搭指南:150小个子显高又时髦的搭配秘诀
- 心灵的旅程:从北京到西藏的搭子之旅
- 在深圳找"学英语搭子"有哪些靠谱的途径?
- 马尔斯健身搭子的乐趣与收获
- 探索上海:寻找完美的“出来玩搭子”
- ### 40岁旅游搭子:重新定义旅行的陪伴
- 重温经典,畅玩“大富翁11”游戏搭子之乐
- “高新区减肥搭子:都市青年的健康社交新潮流”
- 什么是浙江湖州的“搭子”?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