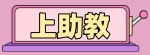
高考完游戏搭子
《高考结束那晚,我和游戏搭子打了一整夜》
最后一科收卷铃响起的时候,我的手还在抖。走廊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,有人撕了复习资料从窗口撒出去,纸片在夕阳里飘得像一场雪。我摸出关机三天的手机,刚连上网,就弹出十几条消息——全来自同一个群聊:「峡谷养老院」。
「考完了没?速上线!」
「老子闪现键都快不会按了!」
「五缺一,演我你就完了!」
这群人是我高三偷偷打游戏时攒下的「患难搭子」。有人是隔壁班的学霸,有人是匹配遇到的嘴强王者,还有个总爱玩辅助的妹子,每次开麦都压低声音说「我妈在隔壁」。我们约好高考前互相监督卸载游戏,但谁都没提考后第一件事要干什么——因为根本不用提。
那晚的网吧比过年还热闹。推门进去就看见角落里五台连坐的机子闪着光,耳机挂在显示器上晃荡,像某种接头暗号。阿凯把冰可乐砸在我面前:「三分钟吃完,第三把给你留了中单。」屏幕上的游戏界面熟悉得让人鼻酸,原来肌肉记忆比知识点更顽固。
打到凌晨三点时,下路突然掉线。两分钟后电话打过来,小琪带着哭腔说:「我爸发现我半夜溜出来…」我们四个对着黑掉的头像沉默三秒,异口同声:「快跑!」第二天才知道,她抱着显示器电源线翻阳台时被当成小偷,差点惊动画了三年重点大学大饼的班主任。
后来我们很少再五排。有人去北方看雪,有人复读,阿凯的账号再没亮起过。但每次登录游戏,系统提示「好友上线」的瞬间,我总觉得能听见那年夏天的键盘声,混着网吧老板的吼叫:「302号机!你妈打电话到前台了!」
与高考完游戏搭子相关的问题
其他问题
- 你们三个平时一起吃饭口味差异大吗?怎么协调的?
- 在东莞长安附近有没有喜欢打台球的搭子?想找水平相近的球友一起练球或娱乐!
- 和游戏搭子聊天时总是冷场,除了聊游戏还能聊什么?
- 什么是“抖音拍摄搭子”?怎么找到合适的搭档?
- 最近对游戏搭子上头了,每天总想找TA一起玩,影响了正常生活,该怎么办?
- “考公搭子陕西:并肩奋斗的‘上岸’之旅”
- 想找稳定的“蛋搭子”四排上分,平时晚上在线,有没有车队缺人?
- ### 转塘台球搭子:友谊与竞技的交汇点
- 《80后的“聊天搭子”:在数字时代找回消失的烟火气》
- 西安雁塔羽毛球搭子:以球会友,挥洒青春与汗水
- 有没有最近从成都出发去四姑娘山的搭子?想结伴拼车或自驾,时间灵活可商量!
- 「广州酒搭子天河:微醺夜生活与城市烟火气的完美交融」
- 什么是“小给子穿搭”?有哪些风格特点?
- 寻找成都到昆明的旅行搭子,畅享美丽旅程
- 《从珠海出发,寻找你的完美旅游搭子:结伴同行,快乐翻倍!》
- 在广东读大学,想找一起学习、运动的搭子,有什么靠谱的途径推荐吗?
- 《寻遍朋友圈,为何找个合拍的旅游搭子这么难?》
- 南宁端午节: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快乐搭子
- 「周口出发,寻找你的旅行搭子!一起探索未知的风景」
- 参加青岛国乙Only展需要提前找搭子吗?怎么找到合适的同好?